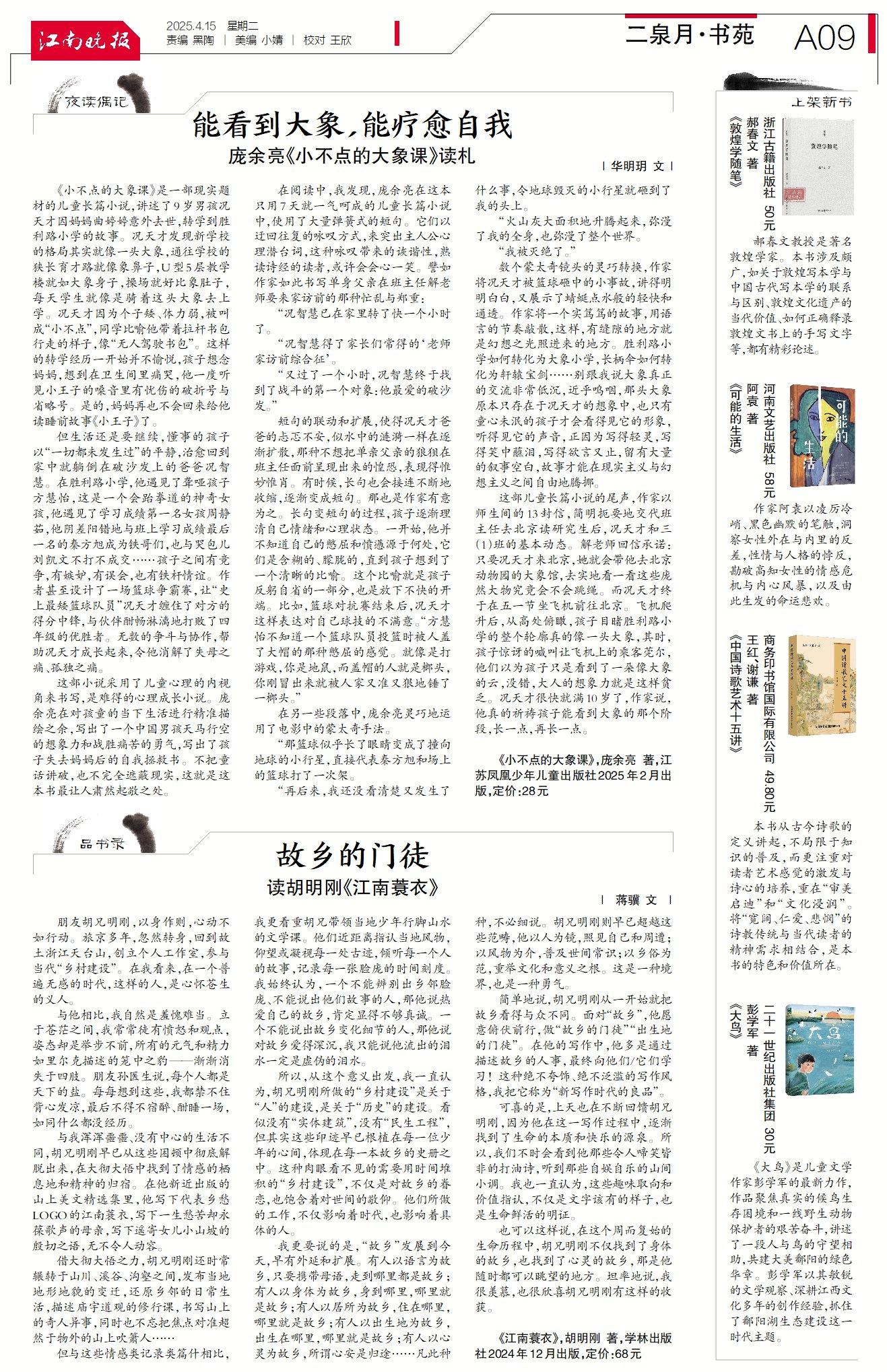| 蒋骥 文 |
朋友胡兄明刚,以身作则,心动不如行动。旅京多年,忽然转身,回到故土浙江天台山,创立个人工作室,参与当代“乡村建设”。在我看来,在一个普遍无感的时代,这样的人,是心怀苍生的义人。
与他相比,我自然是羞愧难当。立于苍茫之间,我常常徒有愤怒和观点,姿态却是举步不前,所有的元气和精力如里尔克描述的笼中之豹——渐渐消失于四肢。朋友孙医生说,每个人都是天下的盐。每每想到这些,我都禁不住背心发凉,最后不得不宿醉、酣睡一场,如同什么都没经历。
与我浑浑噩噩、没有中心的生活不同,胡兄明刚早已从这些困顿中彻底解脱出来,在大彻大悟中找到了情感的栖息地和精神的归宿。在他新近出版的山上美文精选集里,他写下代表乡愁LOGO的江南蓑衣,写下一生愁苦却永葆歌声的母亲,写下遥寄女儿小山坡的殷切之语,无不令人动容。
借大彻大悟之力,胡兄明刚还时常辗转于山川、溪谷、沟壑之间,发布当地地形地貌的变迁,还原乡邻的日常生活,描述庙宇道观的修行课,书写山上的奇人异事,同时也不忘把焦点对准超然于物外的山上吹箫人……
但与这些情感类记录类篇什相比,我更看重胡兄带领当地少年行脚山水的文学课。他们近距离指认当地风物,仰望或凝视每一处古迹,倾听每一个人的故事,记录每一张脸庞的时间刻度。我始终认为,一个不能辨别出乡邻脸庞、不能说出他们故事的人,那他说热爱自己的故乡,肯定显得不够真诚。一个不能说出故乡变化细节的人,那他说对故乡爱得深沉,我只能说他流出的泪水一定是虚伪的泪水。
所以,从这个意义出发,我一直认为,胡兄明刚所做的“乡村建设”是关于“人”的建设,是关于“历史”的建设。看似没有“实体建筑”,没有“民生工程”,但其实这些印迹早已根植在每一位少年的心间,体现在每一本故乡的史册之中。这种肉眼看不见的需要用时间堆积的“乡村建设”,不仅是对故乡的眷恋,也饱含着对世间的敬仰。他们所做的工作,不仅影响着时代,也影响着具体的人。
我更要说的是,“故乡”发展到今天,早有外延和扩展。有人以语言为故乡,只要携带母语,走到哪里都是故乡;有人以身体为故乡,身到哪里,哪里就是故乡;有人以居所为故乡,住在哪里,哪里就是故乡;有人以出生地为故乡,出生在哪里,哪里就是故乡;有人以心灵为故乡,所谓心安是归途……凡此种种,不必细说。胡兄明刚则早已超越这些范畴,他以人为镜,照见自己和周遭;以风物为介,普及世间常识;以乡俗为范,重举文化和意义之根。这是一种境界,也是一种勇气。
简单地说,胡兄明刚从一开始就把故乡看得与众不同。面对“故乡”,他愿意俯伏前行,做“故乡的门徒”“出生地的门徒”。在他的写作中,他多是通过描述故乡的人事,最终向他们/它们学习!这种绝不夸饰、绝不泛滥的写作风格,我把它称为“新写作时代的良品”。
可喜的是,上天也在不断回馈胡兄明刚,因为他在这一写作过程中,逐渐找到了生命的本质和快乐的源泉。所以,我们不时会看到他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打油诗,听到那些自娱自乐的山间小调。我也一直认为,这些趣味取向和价值指认,不仅是文字该有的样子,也是生命鲜活的明证。
也可以这样说,在这个周而复始的生命历程中,胡兄明刚不仅找到了身体的故乡,也找到了心灵的故乡,那是他随时都可以眺望的地方。坦率地说,我很羡慕,也很欣喜胡兄明刚有这样的收获。
《江南蓑衣》,胡明刚 著,学林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,定价:68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