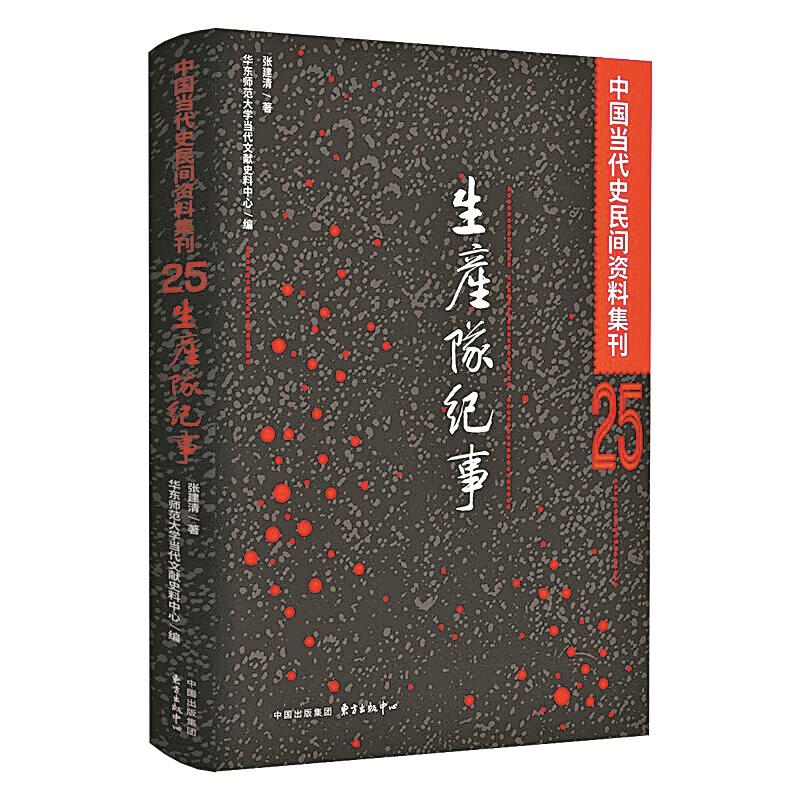□杨文隽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没有“生产队”这个条目。在老版《新华字典》中还是能够查到的,释义是:“在农村人民公社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集体经济领导机构的时候,是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最基本的一级。生产队对本队范围内的土地和牲畜、农具等生产资料享有所有权,在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下,直接组织生产,负责收益分配,独立核算,自负盈亏。”但没有交代其具体存在的时间。
是啊,“生产队”这个名词,早就随着1984年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失了。
21世纪初,张建清将自己储存在脑子里像咸菜干那样的记忆,在茶余饭后唏嘘感慨一番,然后倾注笔端,一则则小故事凑成15万字的《生产队档案》。那时我们坐在玉祁广播站二楼的会议室里,叽叽呱呱讨论着书稿,以亲历者视角共同还原生产队的工分制度、集体劳动场景、物资分配细节、农具管理要点……相信能为研究20世纪中后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提供鲜活个案而激动不已。窗外的雨滴敲打着梧桐叶,而建清眼中的光芒比窗外的雨还要明亮。
二十年过去了,当这本更名为《生产队纪事》的书终于正式出版时,我摩挲着光滑的封面,恍然惊觉:这哪里只是一本书,分明是在填补官方档案中缺失的民间记忆啊。
张建清的笔触有一种特殊的魔力,能将那些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生产队日常,重新赋予血肉与温度。他将方言、民谚、地方性隐喻等元素融入创作,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,以小人物命运折射时代洪流。书中人物,如酒鬼阿林、野猫其人、悍妇阿菊、猪贩洪福、小人阿平、全科医生在集体劳动中展现的人性光辉与局限,通过代际冲突、道德困境等主题引发普遍共鸣,富有超越具体历史的文学感染力。官方档案中找不到这些带着体温的记忆,而张建清用他固执的笔,为我们抢救下了一整个时代的民间表情。
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,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怀旧。张建清没有将那个时代浪漫化,也没有刻意渲染苦难。他笔下的生产队生活,就像江南水田里的泥鳅,既有滑溜溜的狡黠,也有活蹦乱跳的生机。读到他以黑色幽默如《朝气蓬勃》《发泡味精》,以及魔幻意象如《口吐祸福》《进城觅宝》等艺术手法呈现生产队的故事,我们这一代人都会心一笑——那笑容里含着盐分,是岁月腌渍过的苦涩滋味。
作为与张建清相交数十年的文友,我深知这些文字的分量。《生产队纪事》在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、历史在场与文学超越之间找到平衡,兼具档案价值与文学意义。其最大贡献是通过“生产队”这一棱镜,让当代读者理解父辈如何在饥饿、批斗等苦难中构建生活意义,进而反思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博弈。
《生产队纪事》的出版,恰逢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之际。那些曾经维系中国农村基本运转的生产队智慧,那些蕴含在集体劳动中的民间哲学,在今天看来竟有着惊人的现代性。张建清无意中完成了一次文化抢救,他打捞起的不仅是记忆,更是一种正在消逝的生活智慧。
此刻,我的书架上并排放着二十年前的打印稿和崭新的出版物。油墨香里,我仿佛又看见建清谈起生产队往事时发亮的眼睛。他用二十年光阴培育的这株记忆之花,终于破土而出,在历史的春风中摇曳生姿。而我们这些同龄读者,则幸运地成为第一批闻见花香的人。